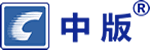近几年,随着“两高”先后颁布司法解释,明确并细化各种形式的受贿行为,实现了对行贿和受贿犯罪行为的精确打击。
与此同时,一种游走于法律边缘,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暗贿赂”却悄然出现。对于“暗贿赂”并没有明确定义,可以理解为行贿、受贿双方通常不进行直接的权钱交易,受贿的载体不直接体现为金钱或财物,而是某种机会、利益或者好处。
有法律专家建议,不妨通过完善法律以遏止这种“暗贿赂”。
送你一个昂贵的“机会”
“举个简单的例子:甲想求乙办一件事情,但不方便直接‘表示’,碰巧甲听说乙的孩子要上名校,甲便先向这些名校捐助一笔钱,获取进入该校的入学名额,然后将入学机会送给乙。就这样,本来清清楚楚的行贿、受贿行为,由于侦查机关很难取得有力证据,最终往往被认定为不是犯罪。”
采访中,沈阳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刘姓检察官告诉记者,随着一些城市升学、择校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化,那些公认的名校的入学资格也成为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有些人便在这上面打起了主意。
记者了解到有这样一起案例: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刘天阳(化名),希望从主管项目审批工作的某单位领导陈宏明(化名)那里获得相应的业务机会。得知陈宏明的孩子面临升学的情况后,刘天阳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陈宏明的孩子顺利进入该名校就读。这样一来,刘天阳帮陈宏明节省了十余万元的择校费用,作为回报,刘天阳所在的公司也“如愿”获得了一些项目。后来陈宏明案发,但本该由陈宏明交纳的十余万元择校费,却未被法院认定为陈宏明的受贿数额。
“由于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好处的形式仅界定为‘财物’,所以刘天阳利用自己的人情关系帮助陈宏明的孩子到名校就读这一情况无法界定为受贿犯罪。”刘检察官说,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这种提供教育资源是“暗贿赂”中最为常见的形式。
刘检察官分析个中原因时说道,名校入学资格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要想获得它不仅需要高额的择校费,往往还需要相应的社会关系。有人需要这种资源,但又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要么没钱,要么没关系,甚至既没钱又没关系。
“而这无形中就给行贿、受贿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刘检察官说,“有的‘暗贿赂’是通过直接替受贿方交纳择校费实现的,还有的行贿方不是用权钱交易,而仅凭人情关系为对方进行教育方面的帮助,这种情况给案件查办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甚至成为棘手问题。”
在上述案例中,尽管十几万元的择校费最终未被认定为陈宏明的受贿金额,但刘检察官认为应该予以认定。他分析说,从表面上看,陈宏明接受的只是刘天阳提供的一个入学机会,权钱交易的因果链被切断了;但实质上,这个机会只是个幌子,不过是利用它把权、钱之间的直接交易掩盖起来了,因此,刘天阳与陈宏明之间仍然是权钱交易,不过是直接的“钱”被替换成了一个“机会”而已。
据了解,与提供入学机会相类似,还有一些请托人给受托人或其亲属提供旅游机会、出国机会、就业机会等诸如此类的“暗贿赂”。
离职领导“再就业”也是“暗贿赂”
为防止腐败期权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与此同时,《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但在现实中,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在退休或离职后到其他企业任职,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障碍,但这种情况到头来往往被利用,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收受好处的“挡箭牌”。
黄成茂(化名)离职前是资源行业一家国有公司的地区主管,享有工程审批权。某公司在其“帮助”下取得了不少工程项目。黄成茂离任后,该公司一次性支付给他100万元,作为将来聘用其担任公司副总的“定金”,双方为此签署了相应的聘用合同。
黄成茂因收受该笔巨款涉嫌受贿犯罪后,他本人和该公司一致表示,黄成茂属于行业顶尖人才,支付如此巨额的定金是为了防止他被其他公司聘用。
由于没有发现该公司与黄成茂之间存在对黄成茂离职后收取好处进行约定的相关证据,最终检察机关不得不对这一案件作了撤案处理。
刘检察官坦言,尽管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如果行、受贿双方就离职后收受财物单独进行约定,或者彼此心照不宣,未进行约定,在缺少相关旁证,行、受贿双方又达成了攻守同盟的情况下,办案机关如何证明双方存在“约定”以及“约定”的内容存在巨大困难。
“暗贿赂”遭遇界定难
刘检察官告诉记者,刑法中并未对“暗贿赂”进行界定,其外延和内涵也不完全确定。因此,“暗贿赂”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
除了定罪难,“暗贿赂”的出现还带来另外一个难题。因为受贿数额是受贿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有些“暗贿赂”的价值很难或无法计算出来,无形中增加了对“暗贿赂”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的难度。
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孙金宝律师指出,罪与非罪之间必须清晰界定,不能留有任何灰色地带。对不同形式的“暗贿赂”行为要具体分析,要么认定为犯罪,要么认定为不是犯罪,而不能模棱两可。
打击“暗贿赂”需完善立法
“暗贿赂”行为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其交易的模式、内容,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权权型交易,即交易双方都是掌握一定权力、能够决定一定事项的官员或具备经济实力的富豪,彼此互送人情,达成一种默契。这种交易往往表面上看起来合法,却有损于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但由于不存在直接收受金钱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第二种是权色型交易。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曾有过将行贿人支付给为受贿人提供性服务的人的金钱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的案例。即便如此,如果行贿人安排单位员工或亲属为受托人提供性服务,受贿数额根本就无从认定。而权色交易更是作为一般的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行为,很少见到因此按行贿、受贿犯罪处理的案例和报道。
采访中,很多受访的法律界人士表示,打击“暗贿赂”行为,严格执法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立法上创新,将认定腐败犯罪的一些苛刻的条件降低。现行法律将贿赂犯罪的对象限定为“财物”,范围过小,如果将其扩大为“利益”,将大大增加受贿犯罪认定的范围;同时,现行法律要求证明受托者为请托者谋取或承诺为请托者谋取利益,加大了受贿犯罪收集证据和证明的难度。
“按照新加坡的法律,只要是受贿者收到好处,法律并不要求证明为对方谋取了正当或不正当利益,其中甚至规定,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是否给对方谋取了利益,只要收了钱或者给了钱,那么贿赂罪就成立。”刘检察官说,“我国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我们叫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财产申报制度,只能通过调查别的贪污受贿案件,发现某人可能有大量的存款、现金,然后按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通过立法创新推动反腐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法律。”
【他山之石】
国外立法遏止暗贿赂
一些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暗贿赂”,因其手段多样、隐蔽性强、形式合法化等特点,被越来越多地作为权力寻租的工具。由于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存在限制条件较多,规制范围较窄,限制了惩治力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对这些行为进行规制,贪腐之风难以得到彻底遏制。
据了解,德国、日本等对贿赂犯罪对象的规定已经不局限于财物,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规定了受贿的对象包括物质与非物质利益。而我国的司法解释对构成受贿犯罪附加了一些限定条件,如离职后收受好处构成受贿犯罪需具有事先约定;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够罪的前提限定为“不实际工作”等情况。这些条件取消并不影响犯罪构成的实现。
此外,应将国家工作人员在对外交往中规范自身行为的各类规定和各种制度建设延伸到日常工作中,成为一种常态性的管理措施和手段,时时提醒其保持清醒,明确行为的基准和底线。
【延伸采访】
给领导挂名也是一种“暗贿赂”
采访中,有受访者提出一种现象:有些人明明是自己写的稿子,却在发表时将领导的名字署在前面,该受访者认为这也是一种暗贿赂。
对此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按照我国现有的有关司法解释,是否构成贿赂一个重要的要件是当事人“索取他人财物”或“给予工作人员以财物”,现在只是用这种署名的形式,而不是“财物”,这就无法认定其为贿赂。
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孙金宝律师表示,“贿赂”并不应仅仅表现在财物上,只要是用来买通别人的任何表现形式都可以认为是“贿赂”,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非物质的贿赂是暗贿赂。
辽宁社会科学院一位陈姓研究实习员分析说,给领导“带名”,看似小事,但其中至少牵涉三方面问题:
一是荣誉问题。荣誉就是名誉。它一般不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但附属在其上面的却是一种无形资产。如少数领导喜欢出人头地,希望经常在报刊上露露面,让上级领导知道自己的大名,知道自己的文采,知道自己的功绩。于是就有一些人心领神会,投其所好,一拍即合。这样,这种长期与所属工作人员“合作”发表文章的领导得到的就是一种荣誉,这就是荣誉贿赂。
二是著作权问题。著作权主体是指依法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专有权利的人,也就是直接创作作品的人。领导虽然没有参与创作,但一旦在文章上署上了名字,就标志着对该文章拥有了著作权。领导没有参与文章的写作,现在不劳而获地拥有了对作品的著作权,这又构成了著作权贿赂。
三是稿费、奖励费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奖励费。随着人们对宣传、广告效应的认可,一些单位对新闻、论文稿件的奖励是相当高的。奖励费是按照文章署名来发放的,既然领导也署名了,当然拥有奖励费。
“这种变相贿赂危害很大。作为领导,你不主动制止下属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就是暗地里怂恿属下,也就是说领导愿意接受这种变相贿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