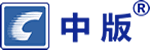今年《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公布,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在音乐界更是引发版权保护与许可的行业争议。同时,《著作权法》与创作者之间的联系在同样具有高创新性和可识别特征的建筑设计领域日益凸显。法治的发展应与全球化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结合,当设计界不断遭遇抄袭、山寨和侵权事件时,创作者需要社会对其知识产权的尊重,法治是创意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知名知识产权与文化创意产业律师,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军律师。
记者:中国国家版权局在今年3月底针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您也曾参加由国家版权局组织的修法讨论。您认为此次对著作权法的修订有哪些进步和遗憾?
王军:去年我作为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的代表也参与了国家版权局召集的修法建议活动。有些意见被采纳,也有一些意见没有在本次修订稿中被体现。有关侵权赔偿的问题在本次修改草案有了积极变化,现有《著作权法》在此问题上存在三难,第一,权利人因侵权造成的实际损失举证难;第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取证难;第三,法院在适用酌定赔偿裁量时,只能在50万元以下做裁量,有效弥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著作权法》新草案中规定,被侵权人可以根据通常的权利交易(许可、转让、特许经营等)的合理倍数来参照确定损失赔偿金额,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酌定裁量的判赔额也有提高,从现有的50万以下提升为100万以下。
就我个人而言,也有两点遗憾。一是有关电影作品保护期限的问题,在西方一些电影产业发达国家,电影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早已从50年提高到70年甚至到90年,而我国仍适用《伯尔尼公约》的原则,规定为首次发表后50年,与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不相适应。二是有关设计作品的保护问题。《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对于作品分类进行了重新梳理,更科学而也更有条理,可惜,现有的作品分类方式仍无法有效保护设计产业。
当然立法部门也有难处,如果将工业设计单纯列项,可能会造成不同类型作品的交叉和重叠,但我依然认为,此次修改草案应至少在作品权利项中引入一个有关设计的兜底条款。现有的兜底条款仅强调了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作品,缺乏对具备结构、外观等独创性美感特征的工业设计作品的保护。实用艺术作品是草案的新增作品类型,指向具有实际用途的艺术作品,但当一件产品设计在案件中存在设计本身属于艺术品还是实用品判断之时,就会产生争议和分歧。目前的很多工业设计,包括家具、服装、建筑设计,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被排除在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之外,显然与立法本意不合拍。
记者:您是否有接受过有关建筑和规划设计方面的法律案件?有哪些独特性和分析价值?
王军:前两年,有两个关于建筑设计的案件具有典型意义,一个是保时捷中国有限公司对泰赫雅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起诉,保时捷中国公司认为被起诉方完全抄袭了其营销店的建筑构造、风格和结构,保时捷公司本身拥有这家公司建筑作品的著作权,要求抄袭方改变结构和外观,并赔偿版权侵权损失。另一个案例是,北京国家体育场,即“鸟巢”本身的建筑设计独特,认知度、识别性高,有浏阳一家花炮厂将大型烟花设计为鸟巢造型,鸟巢设计版权方由此提起版权侵权诉讼。这两个案例最终均以原告胜诉结案。虽然这类涉及建筑设计的法律诉讼案件还不多,但社会中这类侵权行为却是普遍存在的,建筑作品的版权方或建筑设计师通过法律保护自身创作成果的意识还很薄弱。
建筑设计师应该懂法,知道如何使个人作品受到法律保护,也应当了解当被版权被侵权后如何依法维权。很多建筑师并不了解法律诉讼的程序和处理方法,过分担心维权过程中消耗过多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资源。设计作品被侵权后,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手段追究侵权者,在诉讼过程中,也有很多侵权方通过转“侵权”为“补授权”的方式与权利人达成和解。建筑设计与其他作品不同,如果侵权建筑物已经快完工,如果被直接判令停止侵权,那么损失很大,法院一般出于对社会损失的平衡考虑不会直接判令停止侵权,而是判决赔偿损失予以弥补。此外,在建筑设计委托创作或竞标活动中,建筑师应与合作者签订保密协议,这是非常必要的前置程序,在国外很普遍,但在中国,由于法律习惯和商业经验等方面的原因,仍不多见,给未来出现侵权盗版埋下祸根。
记者:进入数字技术时代,信息传递具有匿名性、快速化和广泛化的特征,您如何看在全媒体时代的侵权和保护?
王军:从侵权形式来看,数字时代的侵权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只不过是,他人接触、获得别人知识产权成果的渠道、手段、方式更多样、更便捷、更低成本了,虽说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抄袭者带来便利,但这并不是数字技术本身的错。面对数字传播,版权人应当有更强的确权与权利保留意识。
记者:很多我们通常揶揄的“山寨”概念是否也存在侵权的现象?
王军: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山寨”行为都是侵权行为。“山寨”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分析一个“山寨”产品是否存在侵权时,应首先判断被山寨的作品是否拥有著作权,是否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类型。
著作权法涉及的与建筑设计有关的作品类型其实包括三类,分别为具有美感的建筑物、构筑物,建筑模型,建筑设计图。在两个建筑作品之间发生侵权争议时,法院通常会以三个步骤来认定侵权指控是否成立,第一步是抽象化,著作权不保护思想和创意,但是保护思想和创意的表达形式,要先把思想拿走;第二步是过滤,将不具备著作权特征的社会公共元素从作品者拿走,只保留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内容;第三步是比对,将过滤剩下的独创性内容进行比对,来判断这些独创性内容本身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这是应有的版权侵权判断原则。
目前,在业内的一个分歧是,是否所有的建筑都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一个平庸的建筑作品和一个具有显著创造性特征的建筑作品是否都应受到版权保护呢?从《著作权法》的立法意图来讲,并没有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创作高度,只是强调是否属于原创。当然,作品的创造力越强,识别性越高,作品被版权保护的可能性和力度也更大。
记者:国外的一些设计师可以通过一个作品的创作一生收益,但是中国的设计界则是另一番景象,您认为原因主要存在于哪几个方面?与国外的著作权保护体系相比,我们还有哪些差距?
王军: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为创意之火浇上的利益之油。中国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传统,这和我们的商业环境、文化传承有关。中国自古倡导智力成果的公开分享,“窃书不为偷”,不提倡私有财富化。但实际上,智力成果产权应当作为公民私权的重要内容而被法律保护。
从商业环境讲,任何国家的立法现状都与其现实国情密切相关。应该讲,目前我们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工业及设计业还是更多地在模仿、使用、生产他人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原创知识产权带来的商业价值仍未成为社会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相比于美国这个知识产权输出大国,中国目前仍是制造、使用和消费大国。坦白讲,中国的《著作权法》自1991年颁行,至今仅有20年历史,但是欧美著作权制度已有百年历史,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都和国外存在较大差距。这在立法技术方面也有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部著作权法通常多达数百条之多,而中国目前的著作权法只有61条,调整之后的草案增加到88条,在我们这个成文法国家,88条显然依然难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在立法、修法过程中,我建议更多的行业专家介入,和法律专家共同研讨、分析、判断。法律是要拿给社会来用的,以草案中的音乐版权争议为例,立法环节的概念不匹配势必造成日后法律实施中的脱节和误区,让行业从业者无所适从。知识产权应该被保护,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拥有者应该为其创造性智慧贡献获得社会回报和经济酬劳,至于保护期限、方式和侵权赔偿的司法标准,则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做匹配性衡量,但必须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见性,修法为明日,而不是因为昨日而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