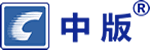作家社再度规模性支付收益 却苦于分成监管缺位———
经济收益,一直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一根敏感神经。这就难怪60余位作家分得近百万元数字版税,能牵扯诸多关注的视线了。数字版权,收益不易,不易于“蛋糕难做大”,更不易于“这块蛋糕”本身是笔“糊涂账”。此度“分钱”,作为内容提供商的作家社,能从数字平台分得几杯羹,全凭数字平台说你们该得几杯羹。一个产业,监管缺位,百分百仰仗“自律”,让人忧虑。
60余位作家获近百万元数字版税
贾平凹、杨红樱、尹建莉等60余位作家近日再次从作家出版社收到2011年数字出版版税近百万元,这是作家出版社第二次规模性给作家支付数字出版版税收益。
早在去年底,作家出版社就已成为了“第一个公开说我吃了螃蟹的人”。当时,天下霸唱、张者、尹建莉、王晓方等一批作家从作家出版社收到了2010年度的数字出版分账收益,最多者天下霸唱获益达到十万余元。那一次,支付额度与今年支付总额度相当。
记者了解到,2010年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尝试性地向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提供300本作品。据作家社介绍,300本作品,涉及两百多位作家,大部分是一人一本,少数作家一人有两三本书。“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纸书上传到手机阅读基地里面收入是零,没有人看,而且不乏名家名作。”
分多少,“故事性”比名气管用
“纵观两次规模性给作家分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规律性的发现,那就是,在纸质出版领域,作家的名气对销量有较大影响,在数字出版领域却收效甚微,作品的故事性本身更能带来收益。”作家出版社副总编刘方称。
刘方说,目前已有10余位作家授权作品的数字版权年度收益接近或超过其纸质作品收益。数字版权年度收益接近或超过其纸质作品收益的,往往是有潜力却还未特别出名的作家。譬如,卫道存、谢林鹤、艾伟、刘小川、武和平、程青等。
“据我们有限的经验,手机阅读,当下大家看得最多的是玄幻的、穿越的。‘标题党’也比较有市场。这与手机阅读人群的特殊性有关。”刘方称,以作家社在中国移动的尝试来看,“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故事性比较强的作品,也较受欢迎。”
分钱,分的是示范效应?
“几十个人分个一百万,这还叫收入啊?”这是作家社给作家规模性支付数字版权收入后得到的网友反馈之一。“我们可能的确不是行业里挣钱最多的。我们信奉的,只是作家提供了作品,就有获益的权利,一个特别朴素的理儿。做的,也就是一件本分的事。这样一种做法,居然引发关注和争议,甚至成为一种事件,本身就不正常。”
据刘方介绍,现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的内容提供商,就有一千多家,涉及图书据称达30多万部,作者数以万计。葛笑政称,经常有作家感叹,社会上大批各类型数字公司追着作家要签数字版权,可一旦将数字版权签出后,约定的作家分账收入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少量拿到一些预付金的作家,签约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合同里约定的版税分成。
刘方说,出版作品之后支付作者版税是出版业诚信经营的基础,但数字出版产业发轫以来,作者的回报和劳动却严重不对称。据他了解,数字出版单位不将数字版税分给作者,有多种原因,例如有的出版社表示数字出版收益本身就不多,有的出版社认为数字出版收益和作家关系不大。“我们这么做,无非是想表明一个态度,行业规范,从我做起。”
怎么分,谁来管?
即便“从我做起”,作家出版社也清楚地知晓,“我”能做的,实在有限。“我们只能确保从我这个环节开始,是公开、公正的。”据刘方介绍,目前,中国移动和作家社的合作中,分成比例是四比六。“这是透明的。”当被问及有无第三方监控收益,刘方称,“说实话不知道,没有人能监控得了,全凭合作方自律。”
刘方称,收益分成不透明,让数字出版规模的扩大面临信任危机。“音乐付费下载、手机彩铃,都存在这个问题。虽然双方之间会约定分成比例,但是到底有多少人阅读、多少人下载、总体收入多少,完全是由对方说了算。有作家说,数字出版可以,但得付出令人满意的首付款,或者说订金。而分成是没谱的事情,分多少完全是对方掌控。不像实体书,出版社说印了多少,你还可以去印刷厂查一下,但是数字版权这块,根本没法查。”
有的作家获得数字版权收益之后,到数字平台上去查作品点击率。“排名靠前的常有几百万的量。有作家说,一本书3块,那应该是几千万的收入才对啊,可我拿到的钱才几万。”刘方承认,点击量跟收益是两码事。“每部作品都有一定比例的部分是供读者免费阅读,不需要付费,也不会给作者带来收益的。”尽管如此,刘方坦承,数字出版分成透明化,确实是一个问题。“有的原创网站,宣称一位作家收益上千万,但他们自己也很难对公众说清楚收益有哪些组成部分。”
刘方表示,许多数字出版平台,譬如自己的合作方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对数字出版产业有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如果让他们在给内容提供商“分成”的时候,完全依靠自律,这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不利。“我期待政府介入行业的渠道建设。这样便于政府监管,也便于建立透明、合理、有效、公平的行业秩序。” |